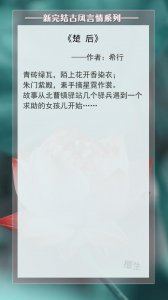蒋韵《我们的娜塔莎》选读 |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蒋韵《我们的娜塔莎》选读 |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无法被湮没的美
庸常生活中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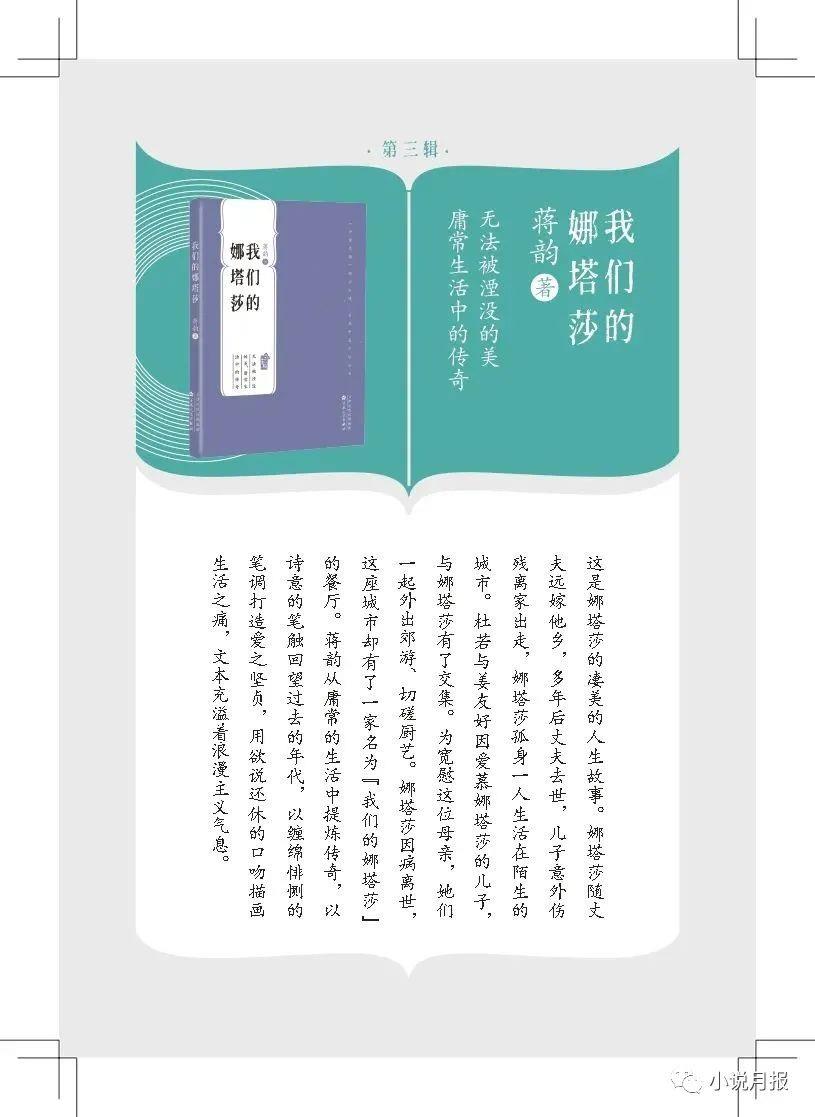
《我们的娜塔莎》
蒋韵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故事梗概
《我们的娜塔莎》讲述了娜塔莎凄美的人生故事。娜塔莎跟随丈夫远嫁他乡,多年后丈夫去世,儿子意外伤残离家出走,远离家乡的娜塔莎孤身一人生活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杜若与姜友好因爱慕娜塔莎的儿子,与娜塔莎的生活有了些许交集,为宽慰这位母亲,她们一起外出郊游、切磋厨艺,最终娜塔莎因病离世,而这座城市却有了一家名为“我们的娜塔莎”的餐厅。作者从庸常的生活中提炼传奇,以诗意的笔触回望过去的年代,以缠绵悱恻的笔调打造爱之坚贞,用欲说还休的口吻描画生活之痛。
小说选读
《我们的娜塔莎》
二 安德烈或者安向东
姜友好是先认识安德烈,后来才认识娜塔莎的。安德烈比姜友好小许多岁,认识他是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时她还在部队,回京探亲,去这朋友家玩,一进门撞上了安德烈。她倒吸一口凉气,惊住了,想,这是哪里?不是北京吗?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古怪的“小妖”?
可是,真好看啊。
那时安德烈也就十三四岁,个子已经很高了。从外形上看,他几乎就是母亲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他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母亲的金发碧眼,在他这里,变成了某种奇妙的棕色,说不出的一种灵动和神秘。朋友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安德烈。”
姜友好失声叫起来:“你怎么配有这样的表弟?”
“嗨嗨怎么说话呢?”朋友说。
这朋友五大三粗,外号“李逵”。
安德烈应该是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的眼光,他知道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异类。他平静地望着姜友好,说道:“我叫安向东。我是哪儿哪儿人。”他说的是那个北方省城。
“巧了,我就在那儿当兵。”姜友好说,“你家住哪儿?”
安德烈说了。
“不过,姐姐,我说了你也不能到我家去,你是军人,你不能去我们家。”
姜友好说:“现在不能去,复员转业就可以了呀。”她望着那个美少年笑了,“安德烈,就冲着你,我也得复员。”
安德烈有点慌了:“你是在开玩笑吧?”
姜友好哈哈大笑:“我当然是在开玩笑。”
可是她真的复员了,还没有服役期满。当然不是因为安德烈。是她实在不适合军人的生活,她天性太自由放浪。起初,当兵是父亲的意志,而复员,则是她自己的主张。父亲没有拗过她,暗地里还是帮了忙,尽管他还未“解放”,但总还是有人脉。结果,姜友好虽然没能回到北京,但毕竟被分配到了那座城市最好的医院里。很快地,在这座城市,她就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有了一群朋友。
是她把安德烈拉进了这个圈子里。
当然,这城市不算大,这圈子里原本也有认识安德烈的人。就像滚雪球一样,你认识我,我认识他,渐渐地,大家就滚成了一团。
安德烈家里没有电话,她写信约他见面,他来了,看见穿便服的她,安德烈说:“姐姐你真的复员了?”
姜友好回答:“当然是真的,”她指指身后医院的大门,“要不你进去问问?”安德烈笑了。这是他们认识后,她第一次看见这个美少年的笑容。她觉得像是突然被阳光晃了眼睛。
“喂,你猜我下一步计划干什么?”她笑着问他。
“干什么?”
“等你长大,嫁给你,”她说,“让你娶我。”
她以为安德烈会大惊失色,会惊慌不已。可是没有。安德烈听了,认真地看着她,摇摇头:“不行,姐姐,”他说,“我不会娶你的,你千万不要等我。”
姜友好哈哈大笑,推了他一把:“逗你玩呢!”她说。不过她马上感到了好奇,“哎你为什么不娶我呀?我不算漂亮吗?拒绝我的人,你可是第一个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好看啊?”
安德烈笑了:“我是好看啊。很多人想当我的女朋友。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才多大就有女朋友了?”姜友好板起了脸,“不能这么早谈恋爱知不知道?”
“你这么说话像我妈妈。”安德烈说。
姜友好笑了:“你女朋友是谁啊?说给我听听。”
“不告诉你,”安德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管将来我女朋友是谁,我都不会娶。我不结婚。”
这下轮到姜友好吃惊了:“为什么呀,安德烈?”
“我不说,”安德烈回答,“不想说。”过了一会他强调,“叫我安向东,这是我的名字。”
这美少年,他不快乐。姜友好想。她其实有点懂得他不快乐的原因。那就让他快乐起来吧。
当天她就带他去了一个聚会,是在一个住在省府大院的朋友家。那天的来人中还真有认识安德烈的,果然是个女孩儿。他们说起学校的事,挖防空洞什么的,那女孩儿的妹妹和安德烈在同一所学校。
“我妹说,你们班男生欺负你,是吗?”女孩儿忽然这么问。
“没有。”安德烈从容地否认。
这个朋友的父母都不在家,刚刚去了“中办学习班”,那学习班在外地。家里没有家长,完全由着他们这些孩子折腾。那天他们煮了一大锅西红柿挂面,开了几个午餐肉罐头,炒了一大盘醋熘土豆丝,戳了两瓶白酒在桌上。大家又吃又喝又吵又闹,但安德烈始终是安静的,滴酒不沾。有人硬把酒杯塞给他,姜友好拦住了,说:
“他还是学生,不能喝酒。”
“靠,咱哪个不是当学生的时候就喝酒了?姜友好你敢说你不是?”
姜友好回答得斩钉截铁:“他不一样。”
“他是不一样,”那人嘻嘻笑着回答,“哪个苏联人不喝酒?”
姜友好顺手把自己杯中的酒泼到了对方脸上。
“姑奶奶说不能喝就不能喝。”
回家的路上,安德烈对姜友好说:“姐姐,其实你不用替我拦着我也不会喝,我答应过我妈妈,我妈说我外公就是一个酒精中毒的酒鬼,那是她的噩梦。我妈说她嫁给我爸和他跑这么远来到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男人不像苏联男人那样酗酒,尤其是那些在苏联的留学生培训生什么的,他们有纪律管着,更是模范。我爸就是没有纪律管着也不喝,他不爱酒。”他停顿了一下,“我也不爱。”又停一下,“我不能爱。”
“安德烈——”
“我是安向东,”他打断了她,“我叫安向东,姐姐。”
姜友好的心里,真的涌起了怜惜。城市的夜晚,黑暗而荒凉,他们同骑一辆自行车,他带着她。她默默地从后面搂住了他的腰,把脸贴在了他完美到无懈可击的脊背上。那一刻,她真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弟弟,这座非亲非故的城市给了她一个混血的、身份难堪的弟弟。她会保护他,她想。安德烈,不,安向东,我会保护你。
可是他出事了。掉进了防空洞里。是被人推下去的。股骨粉碎性骨折。伤愈后,瘸了。
瘸了一条腿的安德烈,变了一个人。
起初,出事时,学校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打了钢钉。那医院从前骨科很强大,但恰逢其时,一切都不正规,手术不成功。情急之下,姜友好帮他转到了自己供职的医院,重新做了第二次手术。
这仍然不算是一次完美的手术。
姜友好天天去病房看他。就是这时候她认识了娜塔莎,也认识了安德烈的妹妹安霞。安霞比安德烈小两岁,和安德烈截然相反的是,猛一看,就是一个肤色白皙的中国女孩儿,五官轮廓完全是父亲的样子,认真看,才能看出她眼睛的颜色是深棕色的,那种接近黑色的、本分的棕,让人踏实和安心。
没有见过安同志。安同志在“学习班”,不能自由行动。
安德烈的腿打了石膏,高高吊着,固定在病床上。他沉默,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来探望他的也都是女同学,姜友好想从她们中间找出那个“女朋友”,却一无所获:她看不出异常,他对她们一样的礼貌和漠然。没人的时候,姜友好忍不住八卦地问道:“哎,哪个是你女朋友?告诉我呗。”
“姐姐你还真信啊?”安德烈冷冷地回答。
那神情和语气,让姜友好感到怪异和陌生。
窗外,麻雀喳喳叫着。树叶开始飘落,天凉了。安德烈望着窗外的天空,忽然问道:
“姐姐,我会不会变成一个瘸子?”
姜友好回答说:“想什么呢?你见过谁骨折了变瘸子的?现代医学治不了癌症还治不了骨折了?”
他嘴角轻蔑地翘翘。
“我有不好的预感,”过了一会儿他这么说,“要是我真瘸了,我宁愿死。”
姜友好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安德烈你听好了,你要再敢说这些话,你要敢这么想,我——”她恶狠狠地瞪着他,“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掐死你?”
他慢慢移开了她的手。
“听我讲个故事,”他说,“就是那年,去北京的时候,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我遇到一个女孩儿。那天车上人不多,我一上来,就看见了她,”他微微笑了,“没有人会看不见她,真美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穿一件蓝印花布中式上衣,脑后梳一根独辫,神态就像仙女。以往,走到哪儿,我都是那个被注目的人,可是那天,她的一双黑眼睛就像巫术一样把一车人的魂儿都吸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比我美丽的人,一个让我呼吸不畅的人……车到了一个站上,停了。她站起来,朝车门走。一车的人这时都倒吸一口气。她摇摇摆摆走着,腿有严重的残疾,一看,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瘸得非常厉害。她在一车人的注视下走完了那几步路,一切都毁灭了,真残忍哪,也真羞耻。我就站在车门那里,因为惊愕,我都忘了给她让路,我永远忘不了她对我说‘请让让’时那种羞惭的神情……姐姐,你愿意让我变成那样?”他望着姜友好说。
姜友好拼命摇头:“你怎么会那样?瞎说,你根本不会变成那样。”但姜友好知道自己是色厉内荏,因为,事情很可能“是那样”,他的状况,不乐观。可她仍然嘴硬:“就算瘸了也不会那样——”
“那是什么样?”他笑了,“你告诉我。”
“你当然还是你——”
“安德烈吗?”他犀利地看着她,“你总是忘了我是安向东,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安向东,可是我永远做不成。假如有一天我回到我母亲的故乡,在那里,恐怕也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纯正的安德烈。我只是个中苏混血儿,对吧?好在我这个中苏混血儿还算好看、漂亮,那是我仅有的一点东西,假如我连这个也没有了,那你让我靠什么活?”
姜友好眼睛渐渐湿了,她握住了安德烈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脸上:“我不知道,安德烈,”她轻轻说,“我从来不追问,我不思考这些,为什么要思考?为什么不尊重生活的神秘感非要破解它?你破解得了吗?傻孩子,你学学我,活得就容易了。”
半年后,八个月后,一年后,最后一次复查终结了,所有人终于放弃了幻想,承认了那个不好的结局。
股骨干严重受伤缺损,加上手术的失败,安德烈的一条腿无可挽回地变短了。比起小儿麻痹后遗症那一类残疾,他瘸得不能算厉害,可是,他不是别人,他是水仙花少年。
他把自己关进房子里,不见人。
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上山下乡。姜友好跟着医疗队去了南部的中条山。临行,她去了一趟他家。可是,他不见她。任凭她怎样敲他家的门,他也不开。只是说:“你走吧,姐姐。”声音平静而冷漠。
他母亲娜塔莎追出来,说:“友好,怎么办?他要毁了。”娜塔莎突然迸出了哭声,“他开始问我要酒喝了。”
她们站在拥挤狭窄的楼道里,对望着,没有谁来救她们。门里,是那个绝望和无辜的、正在放弃自己的孩子,她们束手无策。她们都没有办法还给那孩子完美,神没有应许她们。楼梯旁一小扇肮脏的玻璃窗外,是彩霞满天的黄昏,流金溢彩,美如梦境,一束光涌进来,网住了轻轻哭泣的娜塔莎。姜友好默默地上前,拥抱了一下她,转身离去,她不想让那个母亲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
一年后,等到姜友好从南部乡下回城,再见到安德烈时,她几乎没有认出他来。那是朋友们为她接风的聚会,他来了。姜友好一抬眼,看到眼前站了个陌生人:又高,又臃肿,皮肤粗糙,眼睛混浊,满脸的粉刺,红肿着,浓浓的、不洁的络腮胡须,满身的酒气。姜友好惊得半天合不上嘴,许久,她小心翼翼问:
“我该叫你什么?安德烈还是安向东?”
“随便,”他笑着回答,“哪有那么多事,爱叫啥叫啥。”
他用水杯喝酒,是那种玻璃水杯,满满一大杯白酒几口就光了,和人叫板时,咕嘟咕嘟一口闷,喝得凶猛而贪婪。他就这样无可救药地朝着那个酒鬼的宿命坠落。还没终席,人就像一摊烂泥一样瘫倒在了地上。姜友好想把他拖起来,拽起来,朋友们就说:
“别管他了,每次都是这样,”他们若无其事地说,“开始大家还送他回家,时间长了,就烦了。哎,这次又是谁叫他来的?谁吃饱撑的把他叫来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
没人叫他来,没人找麻烦。可是这不大的城市,他们这些人相聚的地方也就这几处,他总能寻着酒味儿而来,来了,就赶不走他。一个酒鬼的自尊心算什么呢?早就让人踩成一堆烂泥了。姜友好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描述,低头望着地上的那个人,慢慢问道:
“不管他,就是说,就让他这么躺着?”
“对,就躺着呗。”
“那你们走了呢?你们都走了,他还一个人躺在那儿?躺在这脏地上?”
“那倒不会,这几个地方的服务员都认识他,他们有办法吧?大不了把他抬到门外躺着,风吹着酒醒得快。”
姜友好不说话了。她沉默一会儿,然后抬起胳膊指着大门,轻轻说道:“滚!”
他们没听清:“什么?”
“滚!”她大吼一声,“滚——”
“你疯了姜友好?”做东的主人,她父亲老部下的儿子,也喊起来,“为了这么一个中苏混血儿,你六亲不认了?”
她随手抄起一只饭碗,朝地上狠狠一摔,碗碴飞迸:“我以后要是再和你们这群王八蛋交往,我就和这碗一样不得好死!滚!”
“疯子!花痴!你也不看看,他还是以前那个小白脸吗?就这死狗眉竖,你也稀罕?”
“啪”一声,一只碗就飞到了他脸上,登时,那额头上就见红了。血顺着眉骨流下来,流到他眼睛里,虽说店堂里除了他们这桌没几个客人,却也引起一片尖叫、惊呼,乱成一团。姜友好跳到了凳子上,居高临下,指着他鼻子骂道:“?菖你妈满嘴喷粪!你瞎眼了敢欺负我弟弟!告诉你们,谁他妈以后敢欺负我弟,姑奶奶我活剥了他——”
那天的结局是,她的眼睛也变得一团乌青。父亲老部下的儿子一拳砸到了她的眼睛上。人们拉开了他。他也知道对一个女人动粗胜之不武。他们一群人围着那受伤的人走了,去医院包扎。她就坐在那一堆狼藉之中,等着安德烈醒来。
天黑了。就快打烊了。店堂里一片寂静。外面,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寂寞的声音。这城市的夜晚,有种比自然更深邃的荒芜。
一个服务员壮着胆子走到了姜友好身边。
“同志,我们快下班了。”服务员说,“你试试能不能叫醒他?”
就在这时,一个人进来了。姜友好看见那人,“哎呀”一声,得救似的叫起来:“安霞!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安霞说:“我来找我哥。”
“你怎么知道你哥在这儿?”
“我不知道,”安霞安静地回答,“我一家一家找。这个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妈就让我们出来找他。他常去的那几家,我一家一家找,总能找到。”她望着睡在地板上的哥哥,“找到了,就是这个样子……”
姜友好一阵鼻酸。
“嗨,你进来吧!”安霞冲着外面喊了一嗓子。一个大男孩儿应声而入,是个像运动员似的健壮的孩子。“这是我朋友。”安霞对姜友好说,“他会骑三轮车。”
那天,他们几个人合力把他抬到了三轮车上。安霞抱着她哥坐在车斗里,对姜友好说:“我们走了,谢谢你。”
一辆借来的、载货的三轮车,两个孩子,经常在这城市的夜晚,载着一个沉醉不醒的酒鬼,一个酒精中毒者,穿街过巷。男孩儿在前边骑,女孩儿则把那酒鬼抱在怀里坐在后边的车斗里。有月亮或者没有月亮,下雨或者天晴,情愿或者不情愿,没有选择。那是她哥哥。她不幸的亲人。她抱着他就像一个小母亲。
一周后,安德烈来了,来找姜友好。那天是星期天,姜友好在家,她开门看到门外站着的安德烈时,并没有吃惊。她默默地闪身让他进来,她知道他会来。
这天的安德烈,看上去,清爽了一些,至少,衣服是洁净的。他望着坐在对面的姜友好,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七天没碰酒了。”
姜友好没说话。
“可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他说。
姜友好还是没说话,因为她也不知道。
“他们说,你为我打架了。”他看着姜友好那只瘀青还没退净的眼睛,说道,“抱歉——”
姜友好摇摇头:“安德烈,你该说抱歉的人,不是我,”她回答,“你最该说抱歉的,是安霞。”她这么说的时候,鼻子突然酸了。
“我知道。”安德烈闷闷地说,“每次去找我的,去把我弄回来的,都是安霞。我爸不在,我妈不敢去找,她说,她一个苏联女人,满城跑,让别人看见,会给我添更多的麻烦。所以,也就只剩下我妹了……”
“安德烈,”姜友好说,“你不知道那有多让人难过……为了她,戒了吧。”
安德烈沉默不语。
隐隐地,听见了鸽哨的声音,细碎、悠扬。这城市最美的季节到了,秋天到了。天变高了,有了一种别的季节没有的空净澄明。姜友好起身,泡了两杯绿茶,端了来,说:
“喝茶吧,我们家乡的茶。”
他笑了笑,说:“不喝了,我就是来跟你道个歉,走了。”这一笑,隐约地,有了一点从前那个安德烈的影子,“不再打扰了。”
她没有挽留他,她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她仍然没有足够的准备来接受这样一个安德烈。他跛着腿,走到门前,那一跛一跛的姿态,让她心痛。他握住门把手,停了一停,回头说道: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妈妈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子,”他又一笑,说,“那茶的颜色真漂亮,再见——”
他走了。
姜友好后来想,那天,自始至终,他没有叫她姐姐。
那是姜友好最后一次见他。
“他是去跟你告别的。”杜若说。
“是,”姜友好回答,“可我当时没意识到。不久,他跟他妈妈说,想出去散散心,想去爬华山。他妈妈答应了,给了他钱。这一走,从此就没了音信。”
菜凉了,酒也凉了。少年的故事告一段落。杜若起身,热菜、温酒。她端着热好的冬瓜汤回到桌前坐下,姜友好举起了酒杯说:
“添酒回灯重开宴。”
杜若举起杯来,回了一句:“相逢何必曾相识?”
“杜若你这句不对,”夏莲也举起了杯子,“姜友好可不是天涯沦落人啊。”
杜若笑笑,望着姜友好,说:“骨子里是。”
姜友好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重新斟满了,郑重地举到了杜若脸前:“杜若,从今天起,不管你愿不愿意,我是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杜若没有回答,只是把杯中的酒,一口饮干了。酒使她的眼睛里波光粼粼:“姜友好,我能像安德烈一样,叫你姐姐吗?”
“当然可以。”姜友好说。
“姐姐。”杜若叫了一声。突然热泪满盈。
许久,姜友好轻轻说:“杜若,你喜欢安德烈吧?”
雪还在下,纷纷扬扬,天渐渐黑了。她们没去开灯。窗外别人屋顶上厚厚的积雪,闪着微光。杜若望向了窗外,说:“冰天雪地,他会在哪儿?”
“不知道。”
“我喜欢安德烈,姐姐,”杜若说,“是那种遥远的喜欢。就像我喜欢星星,喜欢流云,喜欢江河,喜欢黄山的云雾和古希腊雕像,一句话,我喜欢美。我并不想拥有它们,只是远远地喜欢着,就很满足。但那是今天之前,今天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从今往后,这世界上,多了一个让我牵挂和心疼的人,我心疼他,姐姐……”
姜友好懂。
她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几乎每个星期天,杜若都要来姜友好家,来了,就一起做好吃的。夏莲如果不跑车,也会过来凑热闹。姜友好家是杜若最好的舞台。夏莲从北京输送来的那些肉、蛋之类的食材,正好让杜若大显身手。面对着一桌佳肴,姜友好常常惊叹不已。
“杜若,你小小年纪,这厨艺是跟哪位大师学的?”
“赵佩兰大师,”杜若玩笑地回答,“在下的家母。”
“好羡慕啊!”姜友好说,“有个厨艺如此了得的妈妈,太幸福了。”
“是。”杜若说,“我妈热爱烹饪,而我爸又是个吃货,他的味蕾天生比别人丰富,他俩堪称珠联璧合。所以我妈就是炒一个白萝卜丝,也尽心尽意,比别人炒的好吃太多。就像现在,什么都缺,什么都没有,可我妈总会绞尽脑汁让每一顿饭都尽量可口,因为我爸的人生信条就是:吃饭无小事。”
“听你这么说,我都惭愧了,”姜友好说,“要不,也让我家人帮你家采买东西?让夏莲一块带回来?”
“那怎么可以?绝对不行!”杜若郑重地拒绝,“我爸的另一个信条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那你就把我这里的东西带回去些,咱们分享。”
“更荒谬了。”杜若回答得斩钉截铁,“我爸还有个信条,就是:君子不吃嗟来之食。”
“你爸怎么有那么多信条?”姜友好笑了。
杜若也笑了。
“其实,我爸妈南方老家那边也有家人偶尔会接济我们,给我们寄些腊肉腊肠、霉干菜笋干之类的,而且我们南方人,每人还多供应几斤大米,比起这城市的许多人,已经好太多了。”杜若说,“我妈常说,好日子谁都会过,能把匮乏的、困难的日子过得有尊严又有滋味,才是了不起。”
“你家的人简直都是哲学家,”夏莲笑着说,“简直太恐怖了!”
“你妈这话,我听另一个人也说过类似的。”姜友好若有所思地说。
“谁?”
“娜塔莎。”姜友好回答。
哦,安德烈的母亲。杜若想。那个传说中的女人。
下一个星期天,在姜友好家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杜若进门来,看见一个丰硕的、有些臃肿、远远谈不上美丽的异国女人,正端着一只碗,在搅拌着什么。姜友好说:
“杜若,这是娜塔莎。”
走了这么远的路,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她们遇见了。
作者简介
蒋
韵

蒋韵,1954年3月生于山西,籍贯河南开封。1979年发表处女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你好,安娜》《隐秘盛开》《行走的年代》等,中短篇小说集《心爱的树》《晚祷》《完美的旅行》《水岸云庐》等,非虚构长篇《北方厨房》,以及散文随笔集《青梅》《活着就有眷恋》等。作品曾多次登上《收获》《十月》、中国小说家学会等榜单,曾获老舍文学奖、郁达夫中篇小说奖大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你好,安娜》获2019年度中国好书奖。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西班牙、韩等文字。


1
END
1
新浪微博|小说月报
bilibili平台|小说月报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