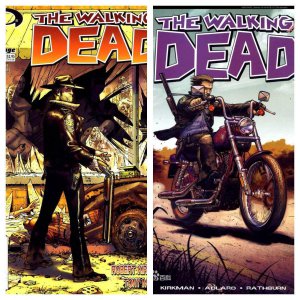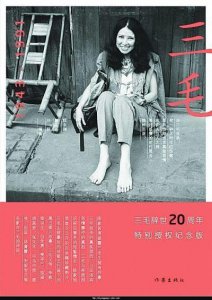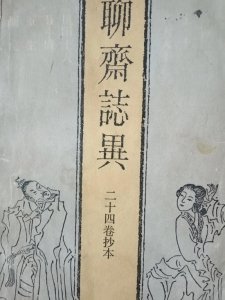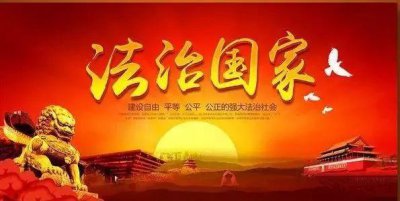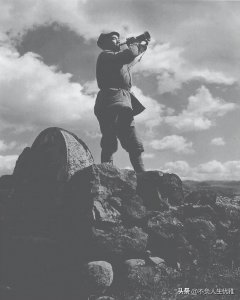山东穷小子,逆袭成首富,身家650亿,给16万员工盖房,为啥
山东穷小子,逆袭成首富,身家650亿,给16万员工盖房,为啥
2021年12月15日,“山东创富榜”揭晓。
在与350名企业家逐鹿争雄中,郑淑良家族以789.3亿元身家,稳坐山东首富宝座。
而且,其名下集团连续10次上榜世界500强。
郑淑良是谁,何以积累起这百亿巨富?
资料显示:她是集团董事长、基金会理事长、张士平妻子。
在这极其简略的介绍背后,蕴藏着财富“真相”:张士平。
他是与柳传志、任正非、曹德旺以及宗庆后,并称为“中国实业界五老”的创一代企业家。

(张士平)
张士平曾在采访时表示:“我始终专注在实体经济上,靠汗水挣钱,不会搞房地产和期货。
我不懂就不做,这是规矩。”
因此,令他发家致富的并不是来钱快、高回报率的投机买卖,而是两个“夕阳产业”:纺织业和铝业。
他35岁开始创业,72岁退休,将一个最初只有61名员工的小棉纺厂,做成如今营收高达4130亿元的综合集团。
因其异常低调的行事作风,张士平一度被外界忽略。
直至2011年、2012年两次摘得山东首富头衔,才猛然引起外界关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中国隐富之王”的传奇故事。


1946年,张士平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一个偏远乡村。
在他成名之前,这里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城市、小县城,为全省乃至全国所做的经济贡献都有限。
如今,邹平县被深深地打上“张士平”的品牌烙印,家乡人向外人说起时,都会介绍这里出了个“很厉害的企业家”。
张士平谈起家乡曾经的贫瘠和落后:
名山大川没有,经济产业也不给力,甚至交通还一度闭塞。
经常挨饿,是他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张士平在这样不利的先天客观环境下长大,初中毕业就不再念书,也没受过任何经商熏陶,浑浑噩噩地跟着父辈种地过活。
穷人家的孩子,最有出息的表现,不过就是凭力气能让自己吃饱饭。
1964年,18岁的张士平开始进厂做事,在县第五油棉厂谋到一份差事。
因为肚子里没多少墨水,只能干些推车、扛棉花等脏活累活。
但在那个年代,有份正当工作,还属于国家集体性质的,算是个让不少人羡慕的铁饭碗。
干得好,就能稳稳当当待一辈子。
小工张士平很满意,干活格外卖力,光膀子挖河沟的轶事一度被传为美谈。
他扛了17年棉花包,一包一百多斤重。
一天要扛少则十几包,多则几十包,很少人能坚持下来,而他却从来不喊累。
平日里,张士平还酷爱打篮球,经常约着工友们在硬石板的篮球场上挥洒青春。
但往往打一场下来,就让本不禁造的布鞋漏洞百出,沦为一次性产品。
那时候,一双鞋得要老母亲焚膏继晷好几个时日才能做好,照张士平这个消耗法,实在供应不起。
于是,心疼母亲的张士平,索性脱了鞋上阵,赤脚飞奔在球场上。

1981年,张士平因“能吃苦、最勤劳”等诸多优良品质。
他从队长、车间主任、副厂长,一步步提拔为厂长。
升官了,但他却没发财,照样老老实实把每月领到的70块工资上交,先是给母亲,后是给媳妇,这都是源于“听父亲的话”。
由此可见,张家虽然家境贫寒,但家风甚严。
这对张士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之后创办的企业都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
35岁当上“大官”,张士平算是三十而立,事业有成了,但真正的辛苦才刚刚开始,辉煌成就才正式起步。
当时国营单位最突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或者说思想觉悟、素质水平的问题。
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士平一点都不含糊:
看不惯工人随地大小便的恶心陋习,他制订了极为严格的车间操守纪律;
对迟到旷工早退习以为常的上工态度,他宣布迟到一小时,罚款一个月工资;
员工顺手吃了厂里收上来准备榨油的花生米,他当即就把人开了,全然不顾这人是某领导的亲戚……
铁腕政策下,这个之前被称为当地“最烂”的厂,慢慢有了正规军的样子。
在张士平看来:
“不管规模大小,效益高低,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粗放式管理。
一直都是西瓜芝麻一起抓,每个环节都仔细小心地管理。”


除了抓内部“小事”,生产大事更不能放松。
那时候,61名职工的油棉厂,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处于赋闲状态。
因为厂里的主要运作方式就是收棉花、加工棉花、再卖出去,过了收棉花的旺季,大家就集体歇着。
张士平觉得这样不行,必须开足马力、全员快进。
于是,在国家放开粮油生产后,他带头搞起异购异销:
到河南、安徽等地收来棉籽、大豆、花生,利用厂里本不该有的空闲劳力将原料榨油销售。
如此一来,一年的另一大半时间被合理利用起来,营收也蹭蹭地跟着往上翻。
同时,张士平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竞争上岗,按劳分配,干得好就留下,干不好就走人,推翻吃大锅饭的传统。
上任短短3年,油棉厂就做到了全国供销工业利润第一,当年利润达400万。
这在之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成绩。
1985年,张士平因其有目共睹的突出表现,被评为全国商业劳动模范,代表全省劳动模范赴京领奖。
这次表彰,被他视为人生中最具意义的奖励。
多年后,当他功成名就,拥有山东首富、亚洲棉王、电力斗士、铝业巨擘等诸多响亮名号。
被问到最喜欢哪个称谓时,张士平依旧憨厚回答:“最自豪的还是全国劳模。”

一家做大后,其它眼红脑热的企业也跟风学起来,棉花加工厂的利润空间被逐步稀释瓜分。
张士平马不停蹄,继续前进,带领团队探索其它盈利点。
有一年,棉花丰收,厂里仓库堆得满坑满谷,张士平回忆:“只能把草一薅,铺上袋子,把多余的棉花放在地上。”
这些一时消化不了的棉花,张士平就为它们开辟新产线,用来制作毛巾;
而后横向延伸,又用来做纺织、家纺、服装等,总之物尽其用,绝不浪费。
张士平的原则就是:“闷着劲扩大规模,压缩成本,一路往前冲。”
1986年,投资设立的毛巾厂,当年实现盈利25万元。
不管是新开发的原料榨油还是毛巾制造,张士平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
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又积极动员大家伙一起出资,最终才把各车间厂子建起来。
搞榨油厂时,靠职工集资10万块买了两套榨油设备;建毛巾厂,再集资89万买了52台织布机。
这对当时只有几十名职工的小油棉厂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集资数额。
很多人是把娶老婆、办嫁妆的老本拿出来,张士平身负重任,不敢搞砸。
然而无论资金多么紧张,他始终坚持以最快的速度购买最先进设备:
“我一点也不心疼,时间比金钱重要,企业要做,就做在前面。”


正是秉承着效率第一的理念,张士平才能次次踩准市场,赢得先机。
借助政策改革,他顺利把国营工厂改制为民营控股、国有参与的公司,创立魏桥棉纺织厂。
很快,这一正确决策的巨大作用就显现出来。
九十年代,国家下达“限产压锭”政策,一些老牌棉厂接连倒闭,整个行业哀嚎一片。
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能活下来就实属不易,应该趁尚未被波及前,赶紧减少投入、收缩规模。
但张士平反其道而行之,他大量引入外资、港资,不断收购这些破产的企业及设备,企业规模不小反大,逆风增长。
对此,不少人说他这是逆天而为,不明所以。
但张士平不急于解释,只对外敷衍解释道:“先收着,以后总有用。”
其实他心里的算盘早就打好了:
国家压缩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产能,像他这个民营小弟,根本不受影响。
反而由于国有资本的退出,给了他做大做强的机会。
5年内,他投入170亿元,将织机从4000台发展到42000万台,纱锭从33万枚增加到500万枚。
经此一役,张士平赢得了“亚洲棉王”的称号。

算盘是打好了,但接手混惯了集体制的老大哥企业,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1998年,张士平收购滨州市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滨州一棉”。
他还没坐进办公室,就先被来了个下马威,厂门口红色条幅上写的不是欢迎词,而是“乡巴佬滚出去”。
张士平没有被唬住,严厉发问:“不让我来,你们想把企业做成什么样?”
当时的一棉厂已经3个月发不出工资,亏损4000万,销售收入不到一个亿,而办公人员却多达300多位,有12个财务。
反观张士平当时的工厂,年销售30个亿,办公楼也才20几人,4个财务。
于是,他到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厂高管全裁了,然后制定最简单也最难做到的死命令:按时上下班。
仅仅这一条,就让很多老员工接受不了。
一些老油条把张士平围在办公楼,提意见、说想法,要求恢复旧制,相安无事。
一名情绪激动的工人质问张士平:“我上夜班睡着了,只迟到了2小时,凭什么扣我一天的工资?”
张士平淡定回答:“这要是在我以前的工厂,要扣一个月。”
多次解释无果后,张士平直接撂下第一次当厂长时说过的话:想干就干,不干就走人。
雷霆之势下,第二年,一棉厂的销售收入增长59.6%,实现赢利4000万,人均劳效是国营企业的5倍。
工厂挣到钱了,职工的工资发下去了,争议自然就停止了。


随后,张士平合并成立魏桥创业集团,立下厂训:
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2003年,集团旗下的魏桥纺织在港交所上市;
2005年,集团登顶成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同年,集团以21.1亿元纯利润,257亿元总资产,跻身福布斯中国顶尖企业榜第六位……
张士平在接受《英才》杂志专访时,被问到:
“做到世界第一后,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他从容地说:“做到世界第一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到世界最强。”
他口中的强者,除了纺织业,还有铝业。
与纺织业双管齐下一同发展的铝业,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
只不过,张士平做什么成什么的优秀体质,把铝业也“顺便”做成了全球领先。
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在入局铝业之前,不得不先提张士平自建电厂的创举。
1999年,受够了被人拉闸限电的被动局面,张士平决定自给自足。
他说:
“我是被高电价和垄断逼上梁山的。过去,用电力部门的电,我们受尽了窝囊气。
电价高不说,还动不动就停电,一点办法没有,求爷爷告奶奶是家常便饭。”
于是,他果断建立起自己的专属电厂。
第一期发电量虽然不大,只有7.8万千瓦/时,但至少避免了长久以来突然断电造成的损失。
然而,如此壮举,自然遭到了淄博电网和邹平县政府的联合警告:
如果执意自行发电,就必须从大电网中解除下网。
在一番博弈争论后,张士平最终决定解列:
“以后他们就管不着我了,我的发电量肯定还要扩大,以后他求我上网,我也不上了。”

脱离“组织”的直接益处,是电价比国网低了1/3,极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
与之相伴的就是不可避免的非议声讨,说张士平自行发电“不合法、不环保、安全性差、未承担社会责任”等。
面对褒贬之声,张士平始终低调处理,一面致信政府机关解释,一面邀请各界人士莅临参观,以实际成果说话。
至此,电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不仅完全够用,还绰绰有余。
因为纺织业务需要大量的热能,耗电量相对较小。
张士平就想再办一家企业来消耗剩余的电能,以达到热电平衡,进一步控制成本。
在考察过电解铝、铜、铁等一系列耗电量大的产业后,最终选择电解铝。
进入新领域,张士平一开始也没什么信心:
“铝业刚起步的时候,就像当年搞纺织一样,受到各方面的排挤,没人相信我们能干成,更没有企业愿意让我们取经。”
又是在一穷二白的不利处境下,艰难开拓。
困难是有,但优势也很明显,铝的电力成本占总成本的45%。
而张士平用自家的电,成本低于市场价,相当于赢在了起跑线上。
身边人都说张士平的发展策略就是“一分钱当一块钱花”。
2001年,公司开通第一条电解铝生产线;
2005年,进入氧化铝领域;
2011年,再探高精铝板新材料领域;
也是在这年,张士平的铝业公司——中国宏桥在香港顺利上市,首日以7.9港元完美收盘。
他由此被奉为“铝业大王”。
随集团产业一同疯狂增长的,还有张士平的身家财富,他手持股值近400亿港元,一夜间晋升为山东首富。
次年,集团首次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他再度蝉联山东首富宝座。


张士平的野心和实力已不止于国内的方圆之地,还大步跨出国门,向海外开拓。
2014年,集团涉足采矿领域。
将非洲几内亚开采的18万吨铝土矿石,通过航运,于2015年冬天,送达山东。
与之前凡事亲力亲为不同,这笔大生意,却不是张士平亲自操刀,而是由他儿子张波全权负责。
因为之前供应氧化铝原料的国外厂家宣布不再出口,集团必须另寻他家。
张波便满世界考察矿区,花费几个月时间,终于搞定了几内亚的项目。
张士平赞到:“从了解到规划,都是儿子一手操办,我完全没参与。
一波三折困难重重,我没想到他能办成。”
不仅儿子能独当一面,女儿也巾帼不让须眉。
当年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女儿张红霞报考时选择了纺织专业,潜心钻研,已成长为不输集团工程师的专业人员。
光是技术过关不算什么,关键还有大局视野。
在这一点上,张士平对爱女刮目相看:
“有一次省领导让我汇报国际与国内棉花的行情,我答不上来,而她却对那些数字了如指掌。”
2016年,在集团的股权结构中:
张士平本人持股36.3%,
弟弟持股2.2%,
儿子张波持股3%,
女儿张红霞持股3%,
女儿张艳红持股1.6%,
女婿持股2.7%;
管理层名单中,张士平家族的数十位成员担任高管职位,妥妥的家族企业模板。
面对外界执意质疑此种团队框架是否合理时,张士平直言不讳:
“既然是民营企业,就没必要避讳是家族企业。
我一向对事不对人,不管是谁,只要能管好这个事,我就用谁。
做企业不能为了避嫌就不用亲戚,也不能因为不是亲戚就不提拔。”
在他看来,任人唯亲的“小爱”,实则是举贤不避亲的“大爱”。

(左张波,右张士平)
2018年9月,72岁的张士平卸任集团董事长,放心交棒给了48岁的儿子张波。
这一年,张士平家族以650亿元财富,位列《胡润富豪榜》第26位。
许多年前,有记者问过张士平,如今铝业的利润早已远远超过纺织盈利,有没有考虑过舍小留大呢?
张士平斩钉截铁地说:
“仅从实力上来看,不要纺织完全可以,还更轻松。
但是纺织厂的员工怎么办?特别是随着智能化的推进,需要的工人会越来越少。
但作为集团董事长,我一直强调不让一个工人下岗,全部安置到其他岗位就业,使他们能平稳退休。”
他对员工的爱护和关注,不止是随便说说、喊喊口号而已:
整个邹平县人口约73万,而集团员工就有16万人,极大程度解决了大部分人口的就业务工问题;
这16万人的住房,全部由集团自建,员工能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居住,到离职时退房还款;
除了家属楼,还配套食堂、幼儿园、医疗诊所等,俨然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很多一家三代人都在厂里工作。
张士平经常自嘲没文化、土,因此特别关照有出息的员工儿女。
就在他退休的这年7月1日,集团下发针对职工子女高考成绩的奖励通知:
高考600分以上的,奖励1万元;
700分以上和滨州市高考状元,大学期间学费全额报销。
如此优渥的连带福利待遇,让不少人慕名而来。
张士平说:“都是农村出来的,我理解他们。
只有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员工才能真心把企业当家。”


让员工把企业当成家,他也就成了员工的家人。
因此,当张士平重病住进ICU时,许多集团员工和家乡当地人都在网上为他祈祷祝福,希望他挺过难关。
然而,命运不通人情。
张士平历经重重艰难,令工厂多番起死回生后,自身却终究没能逃过病魔的考验。
2019年5月23日,张士平因病医治无效,在邹平市人民医院去世,享年73岁。
一代传奇就此谢幕,生前功过是非,全留世人评说。

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是过还是功,不过是站在不同角度的各家评说而已,太过在意只会一事无成。
年华短短数十载,与其瞻前顾后、迟疑犹豫,不如奋力一博、拼个结果。
正如张士平所说“人生没有顶峰,自然也没有退路”。
因此,当下即所有,把握现在才能创造未来。
作者:朱小畅&雯鲛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