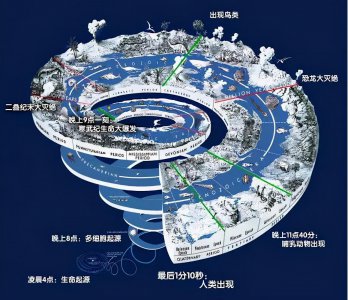白话聊斋:云萝公主
白话聊斋:云萝公主
云萝公主
安大业是河北卢龙人,刚出生就会说话,母亲给他喝下狗血,才止住不说了。
长大后,仪容俊秀,对着镜子自己打量,实在没人可及。天资又聪明,读书成绩优良,名门世家争着想同他结亲。
他母亲得了一梦,说儿子该和公主成婚,深信不疑。
可是到了十五六岁,梦兆一直没有应验,也就渐渐后悔自己过于迷信了。
一天,安大业独个儿坐着,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馨香,不一会儿跑来一个美貌的丫环,说:“公主驾到!”随即用长毯铺地,从门外直到床前。
安大业正在惊疑,只见一个女郎搭着丫环的肩进来,服饰生辉,容光焕发,映照四壁。丫环就把绣花垫放在床上,扶女郎坐下。
安大业惊慌得不知怎样才好,向女郎鞠躬,就问道:“哪里的仙子,屈驾光临?”女郎微笑,用袖子掩住嘴。
丫环说:“这是圣后府中的云萝公主。圣后看中了你,想让公主嫁过来,所以让公主自己来相看宅居。”
安大业又惊又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女郎也低着头:两人相对无言。
安大业平素爱下围棋,棋盘常放在座位旁边,一个丫环用红纱巾掸去灰尘,把它移放在桌上,说:“公主每天迷这个,不知与驸马谁胜?”安大业移坐到桌边,公主也笑着应战。
下完棋,小丫环就笑着禀告公主道:“公主累了,该回去休息了。”
公主就弯下身子对丫环耳语了几句。丫环出去,一会儿重又回来,拿一千两银子放在床上,对安大业说:
“刚才公主说这里的住屋低矮狭小,劳你用这些钱稍加整修,等新屋落成,再来相会。”
另一个丫环说:“这个月犯天刑之忌,不宜兴建土木,过了这个月才吉利。”
公主起身准备离开,安大业拦住她,把房门关上。
丫环拿出一件东西,外形像皮袋,就地鼓气,只见云气突然出来,顷刻间满屋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再想找寻公主,已经无影无踪。
安母知道了这件事,怀疑是妖精,而安大业神颠魂倒,做梦也想,再也不能断绝情丝。
急于修好房屋,顾不上禁忌,限期催促进度,将庭廊屋舍整修一新。
早些时候,有个河北滦县的书生袁大用,借住在安家附近,递上名片求见。
安大业一向极少交游,就借口外出不见,又乘他不在家的时候前去投帖回拜。
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恰巧在门外碰见了,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穿宫绢缝制的单衣,腰缠丝带,脚登乌靴,意态很是优美风雅。
稍稍与他攀谈,十分温文有礼,安大业喜欢他,作揖请他进屋。又请他对弈,互有胜负。下完棋,设酒款待,千杯恨少,谈笑尽欢。
第二天,袁生邀请安大业到他寓所做客,宴席上佳肴上了一道又一道,招待得十分殷勤。
有个小童儿,十二三岁,拍着乐板清唱,又跳跃翻扑作表演。
安大业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走了,袁生就叫小童背他回家。安大业看小童细弱,怕背不动自己,而袁生硬要他服从安排。那小童果然绰有余力,背送他到家。
安大业觉得奇怪,第二天,拿银子赏给小童。小童再三推辞才收下。从此安大业与袁生交情亲密,三两天就来往一次。
袁生为人沉默寡言,而慷慨大方,乐善好施。集市上有人因为债台高筑出卖女儿,他解囊相助,替那人赎回女儿,毫无吝啬之意。
安大业因此更敬重他。过了几天,袁生到安家来道别,赠送了象牙筷、伽南珠等十多件礼品,还有白银五百两,用来帮助修建房屋。
安大业退还了银子,只收下礼物,回赠了五匹绢帛。
过了一个多月,乐亭县有个做官的回乡,行李中满载钱财。
夜间强盗入室,捉住主人,把铁钳烧红了烙他,逼他交出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家人认识强盗是袁生,官府发文四处追捕。
安大业邻居姓屠,与安家不和已久,因为安大业突然大兴土木,暗中起了怀疑和妒忌。
恰好安家有个僮仆偷出一副象牙筷,卖给屠家,屠某知道是袁生赠送的,就报告了县官。
县官派兵将安家宅院围住,正巧安大业带着仆人外出,就抓走了安母。安母年迈体衰,受了惊恐,只剩一口气,两三天不吃不喝。
县官放她出狱。安大业听得母亲的消息,急奔回家,母亲已经病危,过一夜就去世了。
收殓才完毕,安大业就被衙役抓走。县官见他年轻斯文,暗暗怀疑诬告不实,故意恐吓喝问。
安大业如实说了他同袁生交往的经过。县官问:“你怎么会突然富起来?”安大业说:“我母亲有积藏的银子,因为要娶亲,所以装修结婚用房罢了。”
县官信了他的话,就开具公文,将安大业解往郡府结案。
邻居屠某得知他没事,就用重金收买解差,叫他们在路上结果安大业性命。
路过深山,安大业被解差拉到峭壁边,要把他推下悬崖。
眼见得奸计将要得逞、情势岌岌可危,在急难之际,忽然从草木丛中窜出一头猛虎把两名解差咬死,叼起安大业便走。
来到一处,楼阁重重。老虎进内,把安大业放下,只见云萝公主由丫环搀扶着出来,神色凄然地安慰他说:“我想把你留下来,但是你母亲逝世,还没有找到墓地安葬。
你可以把县衙的公文带上,自动到郡府投案,保你平安无事。”
说罢,取过安大业胸前衣带,一连打了十几个结,叮嘱道:“你见了官,拈着这些结一个个解开,可以消灾止祸。”
安大业遵照她的嘱咐,到郡府投案。
太守因为他诚实守信感到可喜,又查看县官的公文,知道了他的冤情,就销去他的罪名,释放回家。
走到半路上,遇见了袁生,便下了坐骑,拉着袁生的手,把别后的情况详述一遍。袁生愤然变了脸色,一言不发。
安大业问他:“像你这样一表人材,为什么要自污品行呢?”
袁生说:“我所杀的都是不义之徒,所拿的都是不义之财。
不然,就是掉在路上,我也不拾的。你对我的教诲固然是金玉良言,然而像你家邻居,岂能留在人间呢!”
说完,飞身纵上坐骑,径自去了。
安大业回到家里,把母亲安葬停当,闭门谢客。
忽然有一夜,强盗闯进邻家,把屠某父子十几口人全都杀死,只留下一个丫环。
强盗把钱财席卷一空,与同来的僮仆分着携带,临走之前,举着灯火向丫环说道:
“你认准了,杀人的是我,同别人没有关系!”并不开门,飞檐走壁而去。
第二天,丫环报了官。县官怀疑安大业知情,又把他捉去。县官口气脸色都很严厉。
安大业在公堂上手捏衣带,一边申辩,一边解结。
县官问不下去,又放了他。安大业回家后,更加藏锋不露,读书不出。只有一个跛足的老婆子为他烧饭罢了。
三年服丧期满了,安大业天天打扫台阶和庭院,一心等待公主的好消息。
一天,满院飘溢奇异的馨香,安大业登上楼阁一看,内外陈设都焕然生辉。他悄悄掀开画帘,已见公主穿戴整齐坐在屋里。
安大业急忙拜见。公主挽着他的手,说:“你不相信命数,妄自大兴土木,结果得了灾祸。又为了尽孝服丧,使我们的结合耽误了三年。急于求成,反而欲速不达,
天下的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
安大业想拿出银子办酒席,公主说:“不必费心了。”
丫环把手伸进柜子,取出的菜肴羹汤都像刚从热锅中盛起似的,酒也香浓清冽。
对饮了好些时候,太阳已经西下,丫环都一个个离开了。
公主四肢娇柔无力,双腿屈屈伸伸,像是无所着落。安大业就亲昵地拥抱她。
公主说:“你先放手。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
安大业搂着她的脖子,问是什么。
公主说道:“如果我们做下棋饮酒的好朋友,可以有三十年的欢聚。如果在床上寻欢作乐,只有六年的团圆。你愿选哪一条?”
安大业说:“六年后再商量吧。”公主就不再言语,于是两情欢洽,成了夫妇。
公主对安大业说:“我早就知道你免不了世俗的选择,这也是定数。”
于是她让安大业带着丫环仆妇,另外住在南院,生火做饭、纺纱织布,维持日常生活。
她住的北院没有烟火,只有棋盘、酒具之类罢了。
院门经常关闭,安大业推它就自动开启,其他人进不去。
然而南院中婢仆干活谁勤谁懒,公主总知道的,常叫安大业去责备偷懒的,没有一个不心悦诚服。
公主不多说话,也不大声喧笑,同她交谈,她只是低着头微笑。每当并肩而坐,她喜欢斜倚着丈夫。
安大业把她抱起放在膝上,轻得像抱婴儿。安大业说:“你这样轻,简直可以像汉代的赵飞燕那样,在手掌上舞蹈了。”
公主说:“这有什么难的!但这是奴婢们跳的,我不屑做罢了。赵飞燕本是我九姐姐的侍儿,好几回因为轻佻而得罪,九姐一怒之下把她贬谪到尘世,又不恪守女子的贞节。现在已被幽禁了起来。”
公主居住的楼阁上布满了锦毯,冬天不曾冷过,夏天不曾热过。
寒冬腊月她都穿轻纱,安大业为她做新衣袄,强迫她穿上,一会儿就脱了,说:“尘世的浊物,几乎要把我骨头压出病来了!”
一天,安大业把妻子抱在膝上,忽然觉得她比往时重得多,很觉奇怪。
公主笑着指着腹部说:“这里头有俗种了。再过几天,她皱着眉说:“这阵子病得胃口不开,倒很想吃点烟火食了。”
安大业就为她准备了可口的菜肴。从此公主的饮食就不再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一天,公主告诉安大业说:“我的体质单薄,受不了生孩子的苦楚。丫环樊英的身子骨挺结实,可以让她代我分娩。”
就脱下贴身衣服让樊英穿上,把她关在屋里。
一会儿,听见婴儿呱呱啼哭,开门一看,生下的是男孩。她高兴地说:“这娃娃一脸福相,必成大器!”于是就取名“大器”。
她用裹住孩子,递到安大业怀里,让他交给奶妈在南院里喂养。
公主打从生下大器后,恢复了当初的细腰,又不再吃烟火食了。
有一天,公主忽然向丈夫告别,要暂回娘家省亲。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回答说“三天”。跟从前一样,鼓动皮袋,消失在云雾之中。
三天到期,不见她归来;一年多过去了,音信全无,安大业也已经绝望了。
他闭门苦读终于中了举人,却始终不肯另娶妻室,常常住在北院里,沉浸在公主留下的余香之中。
一天晚上,安大业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成眠,忽然看见灯火照亮了窗户,房门也自动打开了,一群丫环簇拥着公主进来。
安大业喜出望外,从床上赶紧起身,嗔怪公主失约误期。公主说:“我没有过期,天上才只过了两天半呢!”
安大业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自己考场高中,以为公主一定喜欢。不料公主神情忧郁地说:
“这种身外之物,要来何用!它既不值得骄傲,也不值得沮丧,只能折人寿命罢了。三日不见,你跌进世俗的魔障又深一层了。”
安大业从此不再追求功名利禄。
过了几个月,公主又要回娘家,安大业恋恋不舍,很是难受。
公主说:“这次去一定早早回来,不劳你望眼欲穿。况且人生聚散都有定数,有所节制就久长,恣意放纵就短暂。”
去后,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从此一年半载就回娘家一次,往往几个月才归来。安大业习以为常,也就不抱怨了。
不久后公主又生了一个儿子。她抱起小儿子一看,说:“这是只豺狼啊!”立即叫人把孩子扔掉。
安大业不忍心才作罢,取名叫“可弃”。可弃才满周岁,公主就急忙为他选择婚配。
媒人们前脚刚去后脚来,公主问了对方的生辰八字,都说不适合。
公主说:“我想为狼子修个深圈,竟找不到,只好让他败六七年家,这也是天数!”嘱咐丈夫道:
“记住,四年以后,侯家生个女儿,左胳肢下有个小疣的,就是可弃的媳妇。该把她娶来,不要计较门第。”
就叫安大业记下备忘。后来,公主又去娘家省亲,竟不再回来。
安大业常常将公主的嘱咐告诉亲戚朋友。果然到时候有个侯家的女孩,生来左胳肢下有小疣。
侯家门第卑贱,行为不端,大家都看不起,安大业竟然请媒人定了亲。安大器十七岁进士及第,娶云氏为妻,夫妇两人都孝敬老人,友爱兄弟,安大业钟爱他们。
可弃渐渐长大,不喜欢读书,总是背着父兄,与无赖子弟赌博,常常偷东西还赌债,父亲发狠打他,到底不改。只好互相告诫,防贼一样防他,不让他得手。
可弃就在夜间外出,做穿洞爬墙小偷小摸的勾当,被主人发觉,绑送到县官那儿。
县官审问得他的姓名,用名帖将他送回家,父亲、哥哥一起动手,把他捆起来,狠狠抽打,几乎断气,哥哥代为哀告求免,才放了他。安大业气怒得病,食量锐减。
于是他给两个儿子立了分家产的文书,将楼房良田都分给大器。
可弃怨恨,竟在夜间持刀闯进大器屋里,想要谋害哥哥,却一刀误中了嫂子。
先前,公主有条裤子留在家里,质地极为轻柔,云氏拿来当睡裤穿。
可弃这一刀正砍在睡裤上,火星四溅,吓得拔腿逃去。父亲知道后,病情加重,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人间。
可弃听得父亲病死了,才回家。安大器待他十分厚道,而可弃却更加放肆。
过了一年多,他把所分得的田产挥霍得差不多了,便到郡府去告了哥哥一状。
知府清楚他的为人,将他赶出衙门。兄弟之情就断了。
又过了一年,可弃二十三岁,侯家的女儿也十五岁了。
做哥哥的想起母亲的嘱咐,想赶快给弟弟完婚。他把可弃叫到家里,清扫一处好房子给他住,迎娶侯女进门,又把父亲留下的良田全部登记入册,交给新娘道:
“这几顷薄田,为你拼着命守到今天,现在全都交付给你。我弟弟品行很差,就是给他一根草,他都保不住的。今后家庭兴旺还是败落,全在你新娘身上。如果你能让浪子回头,那就不愁冻饿。不然的话,我这个做哥哥的也填不满他那无底洞啊!”
侯氏虽然是小户人家的女儿,然而天资聪明,容貌秀丽,可弃对她又怕又爱,她说什么不敢违拗。
每次可弃外出,她总是限定时刻,超过时间,就痛骂一顿不给饭吃。可弃因此稍为收敛了一些。
过了一年多,侯氏生了个儿子。她说:“我以后没有什么要求人的了。
良田数顷,我们母子何愁得不到温饱?没有男人,也可以过!"正碰上可弃偷了家中粮食出去赌,侯氏知道了,弯弓搭箭等在门口不许他进来。
可弃吓得抱头鼠窜,窥探妻子进了屋,才畏畏缩缩也进来。
侯氏操起一把刀,起身就砍,可弃连忙扭头奔逃。侯氏追出去砍他,削断了后襟,砍伤了屁股,鲜血沾湿了鞋袜。
他气极了,跑到哥哥那儿诉说,大器不理睬他,只得一肚子委屈满脸羞惭地离开。过了一夜又来了,跪在嫂子面前痛哭流涕,求云氏到妻子那儿去说情,但侯氏却坚决不许他进门。
可弃怒不可遏,声言要去把妻子杀了,大器也不接口。可弃气冲冲地站起身,拿了一杆长矛夺门而出。
云氏吃了一惊,想要制止,大器使眼色叫她别管。
等可弃走远了,才说:“他这是故意摆摆样子,其实哪有胆量回家!"一面派人去看,说是已进了家门。
大器才神情紧张起来,正要赶过去,却见可弃已经气喘吁吁地进来了。
原来可弃闯进家门,侯氏正在逗弄儿子。望见他,就把孩子扔在床上,找到一把菜刀迎上前去。
可弃魂飞魄散,倒拖着长矛掉头就跑,侯氏一直追出门外才返身回屋。
大器早已心里明白,故意问他回去的情况。可弃不说话,只是对着壁角呜呜哭泣,眼睛都哭肿了。
哥哥不禁心生怜意,于是亲自领着他去,侯氏才算收容了他。
等到大器走了,她罚丈夫长跪在地,要挟他发重誓痛改前非,然后才用瓦盆盛了饭给他吃。
从此以后,可弃改恶从善。侯氏亲自经营家业,掌握家政,日子一天天富足起来,可弃坐享其成而已。
后来他七十岁了,子孙满堂,侯氏还常常扯住他的白胡子,罚他跪着走呢。
异史氏说:悍妻妒妇,碰上的就像骨头上生了疮,要倒一辈子的楣,死而后已,难道不毒么!然而砒霜、附子,是天下的剧毒,如果使用得当,头晕目眩也能治愈,不是人参、茯苓所能及的。不过,不是仙人洞察肺腑,又有谁敢把毒药留交给子孙呢!
济南章丘李善迁举人,从小豪爽风流,不拘小节,弹琴吹笛唱曲之类,样样精通。
他的两个哥哥都中了进士,而李举人却愈发不检点。娶了个夫人姓谢,对他稍稍管束严格了些,他就离家出走,三年不回来,到处寻觅,不见踪影。
后来在山东临清县的妓院里找到了他。家人进去见他朝南坐在上座,左右有十来个年轻女子侍候着他,原来都是拜他为师来学习唱曲的。
临走,好几箱衣装,都是妓女们送的。回家后,谢夫人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把书本堆满一桌,同一根长绳一头系在床脚上,一头从窗槅间引出,穿在大铃上,结扎在厨房里。
凡有什么需要,就踩一下绳子,绳动铃响,便有人来应。谢夫人亲自开了个当铺,自己坐在帘子后,收进的东西她估价,左手拿算盘,右手握毛笔,老仆人不过跑跑腿而已。
就这样,积下财货,终于致富,她每每以自己不及两个妯娌显贵为耻辱。在书房中关了三年禁闭,李举人终于考上了进士。
谢夫人满心欢喜说:“三个蛋孵出两只鸡,我还以为你是死蛋呢。今天你也破壳了么?”
又,进士耿崧生,也是章丘人。他的夫人常常挑灯夜织,伴丈夫攻读:纺织的不停工,读书的也不敢休息。
有时朋友故交来拜访,夫人总是躲着偷听:讨论文章就泡茶做饭款待;如果任意说笑,夫人就恶声恶气下逐客令了。
耿崧生每当考试成绩一般,就不敢跨进卧室门内;成绩超等,夫人才笑逐颜开地迎接丈夫。
耿崧生开馆教书,得到的薪酬全数上交妻子,丝毫不敢隐瞒私藏。所以对东家的酬谢,常常当面一分一厘地计较。
旁人有的讥笑他,实在是不了解他对夫人难以交账的苦衷。后来耿崧生为岳父请去,教自己的小舅子读书。
这一年小舅子考取了县学,岳父就给耿崧生送来了十两谢金。耿崧生只收受了酒菜,退回了银子。夫人知道了,说:“他们虽是近亲,然而教书应当收报酬,不然为什么叫'舌耕’呢?”硬是把来人追回来拿下了十两银子。
耿崧生不敢争辩,但心里总觉得内疚,就想暗地里贴还岳父。从此他每年教学馆的收入,都克扣了数目上报夫人。
接连两年多,私房钱已积蓄了若干,忽然梦见有人对他说:“明天去登山,可以凑满金额。”
第二天,试着登高一望,果然拾到人家失落的银两,正好符合缺额。这才偿还了岳父。后来耿崧生中了进士,夫人还呵斥谴责他。
耿崧生说:“我现在已经做官了,你怎么还是这样?”夫人说:“谚语说得好:'水涨船高。’就是做了宰相,难道就大了么?”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