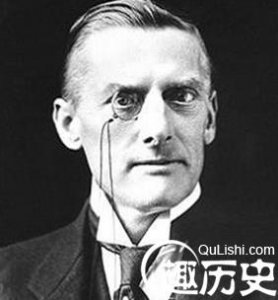「段老师的普法头条(六)」 米兰达规则的起源与进化
「段老师的普法头条(六)」 米兰达规则的起源与进化
“你有权保持沉默!”
空旷的房间里,他双手抱拳撑着下巴,眉目凝重。从今早起床开始,空气中便漂浮着一股吊诡的气氛,他感到全身传来异样的不适,似在提示他,他曾经刻意掩埋的那件事已经在隐隐悸动,而今天将昭示着一切终于浮出了水面。他的自由生活,也即将走向终点。他深吸一口气,说不上内心在思索什么,或许是在策划如何逃过这一未来,抑或是在消极地等待这一宿命。
仿佛为了迎合他内心的恐惧一般,急促的敲门声在这一刻传来了,他混乱的思绪戛然而止,战战兢兢地,他起身,用怪异的步伐走向门前,伴随着“吱呀”一声,门打开了,面前是数位轮廓分明的高个子男人,身上的制服宣示着国家机器的肃杀。
为首的一个男人将逮捕令树在胸前,在简单陈述了涉嫌的罪名后,随即说了几句过往只在媒体电视上耳闻过的话语:“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对任何一个警察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利在接受警察讯问前委托律师,律师可陪伴你受讯问的全过程,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只要你愿意,将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
很多人都对这几句经典的话毫不陌生,单是TVB和美剧中的刑侦类型(两个地区刑侦剧中所说的话还有微妙的不同)就足够让我们对它们“审美疲劳”了。或许有些朋友还特意去网上搜索了这一经典语句的来源,进而了解到一个似懂非懂的名词“米兰达规则”。严格来说,这几句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的固定词语,称为“米兰达警告”更精准一些,而米兰达规则则是衍生米兰达警告的制度基础。
案件起源: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的具体过程
米兰达规则确立于属于典型英美法系的美国。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比较强调“判例”的作用,即一旦一个判决形成,便会根据“遵循先例”的逻辑具有与立法等效的作用。而后续只有在产生新的坚实理由时,才能依据新的判例推翻前述判例。因此,在英美法系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具有与立法相类似的职能。米兰达规则的确立过程即是在判例基础上形成的,这便是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米兰达是一位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全名为埃内斯托·米兰达,居住于亚利桑那州。1963年3月3日深夜,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生了一起暴力强奸案,受害女孩被罪犯强行拖入其驾驶的汽车后座,捆绑手脚后强奸。在后来的报案中,受害女孩将罪犯形象回忆为“约30岁,戴眼镜,墨西哥裔”,驾驶的汽车则为“五十年代早期的福特或克莱斯勒牌轿车”。案发一星期后,受害女孩偶然间目击到与自己被强奸时同款的私家车,车主人的室友即是米兰达,且有犯罪前科。
警方安排女孩进行了“排队”辨认(将犯罪嫌疑人安插在其他人员中由受害者进行甄别),受害女孩当场指认出米兰达。在经过两小时的讯问后,米兰达亦承认了强奸的指控,并在纸面文件上签字,该文件印有如下内容:“我在此做所的陈述是完全基于自愿,未受到任何威胁、胁迫或豁免承诺,我充分了解我的合法权利,了解在这过程中所做的任何陈述可能对我不利。”但是,在讯问过程中,米兰达并未被明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未被告知所做的陈述可能作为不利的呈堂证供,警方也未告知他可以寻求律师帮助。
本案进入审判环节后,米兰达签署的认罪文件被作为重要的有罪证据,但米兰达的律师认为,由于被告人在审问前未被告知上述宪法权利,被告人的供述是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该证据应该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但审理法官认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所谓“沉默权”并不适用于被警方拘押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判决米兰达有罪。该案经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上诉后,仍然维持有罪判决。米兰达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判定米兰达供词无效,该案被发回重审。但是,由于米兰达的女友出庭作证,提供了对他不利的其他证据,米兰达在供词被判无效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有罪标准,最终米兰达仍被判有罪,服刑11年。
该案确立了“米兰达规则”,自此之后,“米兰达警告”成为美国警方在逮捕嫌疑犯时的惯常程序。有意思的是,米兰达在出狱4年后,于一次酒吧斗殴事件中被刺身亡,警方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但该嫌疑人依照米兰达规则选择保持沉默,警方因此而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证据,最终未起诉任何人。
规则形成的过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投票表决
决定米兰达规则最终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投票表决。与2015年美国这几位老态龙钟的大法官决定了同性恋婚姻的未来一样,当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是9位大法官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规则决定的,最终的结果是5:4,仅一票之差。
多数派意见是建立在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不得自证其罪条款和第六修正案的获得律师帮助权条款进行解释的基础上的。由于米兰达在讯问前未被告知相关权利,他的供述应当被视为“毒树之果”。所谓“毒树”,在美国被形象地称呼那些在刑事司法中以非法的程序或手段进行的侦查过程,而“毒树之果”则被喻为在非法手段下获取的证据,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证据不得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
与之相反,少数派意见更为在意的是确定此规则将会产生的社会风险问题。数位法官认为多数派意见是对当时美国的刑讯逼供问题的“过度反应”。他们认为,一旦米兰达规则成型,将会对从今以后的刑事案件树立一个极不好的范式,多数犯罪嫌疑人会受此规则鼓励而更倾向于采取沉默的态度应对讯问,进而导致刑事案件侦破率下降。这种担忧并非无中生有,在米兰达规则确立以后,确实出现了数个已经判决的案件被迫按照米兰达规则推翻的情形。
不管如何,米兰达规则最终以一票之差通过了。时过境迁,以如今的眼光审视这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博弈,或许还能获得一些其他的启示。与笔者曾经普及过的排除合理怀疑、非法证据排除、证据链等现代刑事规则一样,米兰达规则也是在捍卫一个略微反常识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宁愿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换言之,如果针对某个案件获取证据的证明力是或然性的——既无法完全确定一个人是无辜的,又无法完全确定一个人是有罪的,那么法律倾向于选择后者。
“米兰达警告”与“米兰达规则”
经过本案后,米兰达规则正式成型。它的规范表述包含如下四点内容,考虑到多数读者并不具有法学知识背景,笔者尽量以最为通俗的语言进行描述:
1.警方应当明确告知被拘禁中的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权,否则警察不得讯问,由讯问获得的口供无效。
2.犯罪嫌疑人表示沉默时,讯问必须停止。
3.犯罪嫌疑人行使获得律师帮助权时(犯罪嫌疑人自己聘请,无能力聘请时则为其指定律师),在律师到达前,讯问必须停止。
4.如果当犯罪嫌疑人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有所供述,警方有责任证明这些供述是在犯罪嫌疑人明知其享有权利而自愿放弃地情况下做出的。
米兰达警告是米兰达规则的衍生物。由于该规则要求警方在拘禁犯罪嫌疑人时必须迅捷且明确地告知其相关权利,才进而衍生出本文开头那番如今已是司空见惯的话语。坊间传言,米兰达规则刚刚确立时,美国很多基层警察并无法迅速地背过上述那些拗口的话,于是很多警局将这些话语印在逮捕令的背面,在警方为犯罪嫌疑人出具逮捕令时,可以直接念出印在后面的米兰达警告。
米兰达规则的演化与对抗
在英美法系传统中,很多法律制度难以通过一个简化的语言去概括。在我国以及德国、法国等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众多国家,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通常都能找到现实立法作为规范依据,只要看懂相关法律条文,规则的基本内容便清晰了。但在美国,由于并不重视法律文本的作用,很多规则是以法官判例的形式确立的,且这种判例通常并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会通过后续的一系列判例对其进行完善和改进。对一个法科生来说,笔者对这点的印象尤重:当学习来自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时,笔者面对的是一系列内容明确的法条;而当研修英美法系的同一规则时,我却要面对一个又一个冗长的案例和判决,当费尽心思读懂第一个判例,正庆幸自己有所收获时,又经常看到下一段写着“在N年后,该判例又被某某案推翻了……”
而在米兰达规则中,美国的这一判例传统也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后,又在后续通过一系列的新判例对米兰达规则进行了调整、修正和改进,而这一系列米兰达规则的“进化”,却并不像米兰达规则本身那样人尽皆知。相比一个内容较为明确的“米兰达警告”本身,这一系列判例的演变过程其实更能代表美国司法的精神内核: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经验对规则进行不断地完善,最终实现对公正矢志不渝的追求。
几乎是从米兰达规则甫一确立开始,来自美国刑侦界的各种逆反心理即开始作祟。其原因也可以想见,毕竟米兰达规则实质上增加了美国警察的现实侦破困难,对于这一由九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法官做出的判例,警界可是窝着一股火呢。
正因如此,美国警察们开始调动他们那些掉节操的黑暗智商,以各种花样对米兰达规则进行“规避”。当时比较常用的一个做法是开展“二次讯问”,进而延后米兰达警告的时间。即在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后,首先开展第一次讯问,直到警察获得了必要的嫌疑人供述,然后才进行米兰达警告,在警告后才开展第二次讯问。这么一来,由于有利于侦查的供述已经事先获得了,此时犯罪嫌疑人再行使沉默权也于事无补。甚至还有更加离谱的事情:会在正式讯问前通过各种方法为犯罪嫌疑人“施压”,比如令警察假扮受害者对犯罪嫌疑人做出了指认,给犯罪嫌疑人以“犯罪证据已经十分充分”的假象;随即再开始米兰达警告,此时在心理重压下的犯罪嫌疑人便更倾向于做出认罪的供述。在这种做法十分普遍之后,米兰达规则增加了如下要求:如果当犯罪嫌疑人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有所供述,警方有责任证明这些供述是在犯罪嫌疑人明知其享有权利而自愿放弃地情况下做出的。自此之后,这一侦查谋略才偃旗息鼓。
美国警察对抗米兰达规则的行为还衍生出很多政治游说运动。当时的美国政治保守派成员即旗帜鲜明地表明,米兰达规则降低了警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美国的犯罪率。这些政治游说运动在1968年还实质影响了现实立法,1968年的《联邦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即希望推翻米兰达规则,将犯罪嫌疑人供述效力的判断回复到米兰达案以前的标准。但该法的相关规定并没有实质得到执行,相关“野心”也不了了之。
米兰达规则的“纠偏”运动
随着司法实践的推行,除了对美国警察的对抗行为进行纠正外,米兰达规则自己也在发展,即通过新判例的形式对米兰达规则的内容进行“纠偏”,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警察因为该规则而产生的侦查困难问题。从这一系列判例就可以看出来,即便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也无时不刻都在衡量司法中的程序正义和现实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防止由于过于对僵化程序的盲从而损害公共利益。
这一系列纠偏运动中最为知名的有1984年的两个判例,它们确立了在如下两种例外情形下,米兰达规则无需适用,即“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公共安全”的例外。
“必然发现”的例外确立于1984年的尼克斯诉威廉姆斯案,威廉姆斯是一起在戴斯莫尼斯诱拐并谋杀未成年女孩的犯罪嫌疑人,警察依程序逮捕了威廉姆斯,并当场向其宣读了米兰达警告,当时负责搜查的警察尚没有找到女孩的尸体。警察通知了威廉姆斯的律师要把嫌疑人带回戴斯莫尼斯,在押解威廉姆斯的路途中,威廉姆斯自愿告诉了警察尸体的位置。而此时,负责搜查尸体的警察距离尸源地仅差2英里。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辩护人认为威廉姆斯在押解途中的供述证据应被排除,因为米兰达规则要求“犯罪嫌疑人行使获得律师帮助权时,在律师到达前,讯问必须停止”,而威廉姆斯对女孩尸体位置的供述恰恰是在律师未到达前做出的。但该辩护没有得到认可,最高法院因此确立了“必然发现”的例外规则,因为即便没有威廉姆斯的供述,女孩的尸体也必将被搜寻尸体的警察发现。
“公共安全”的例外确立于1984年的纽约州诉夸尔利斯案。当时纽约市皇后区正在巡逻的两位警察接到了一名妇女的报案,声称被一名黑人男性强暴,并说他刚刚进入一家超市,此人身上带有枪。警察按照妇女形容的外貌很快找到了这名犯罪嫌疑人,并进行了拍身检查,发现嫌疑人身上有一个空枪套,其中一位警察问:“枪在哪里?”嫌疑人指了指墙角的一堆空纸箱说:“枪在那里。”警察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那之后才进行了米兰达警告。该案进入司法程序后,辩护律师提出“枪在哪里”的讯问是在告知米兰达规则之前进行的,依此取得的证据应当被排除。该案经纽约州三次审理均判决应排除相关证据,但在联邦最高法院予以推翻,裁定意见认为在本案情况下,公共安全受到紧迫的威胁,“要求嫌疑人回答问题的需要显然超过了遵循米兰达规则的需要”,由此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公共安全”的例外。
米兰达规则未来的可能性
除了确立上述若干例外规则之外,米兰达规则也在适用过程中呈现出渐趋宽松的趋势。在2010年的佛罗里达州诉鲍威尔案中,警方在讯问前做出了米兰达警告,但该警告的内容却略有瑕疵,它没有精准地将米兰达规则的全部内容传达清楚,其中并未告知嫌疑人有在讯问期间要求律师到场的权利。辩护人以米兰达警告并未明确传达嫌疑人享有的相关权利为由做辩护,但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这一判例表明,对米兰达规则的判断不能“机械地抠字眼”,而是应该整体性地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理解了他实际享有的权利。
米兰达规则的这一系列演进清晰地展示出美国司法实务中公共利益和程序正义的博弈,通过一系列例外对米兰达规则的补充和适用过程中的宽松态势,美国司法实际上是在确保捍卫现代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同时,又不对必要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有所妨碍。如今,米兰达规则已远不是美国司法的特色制度,而是影响各英美法系国家乃至大陆法系和我国司法的重要规则,甚至已经是现代刑事司法精神的代名词。在中国,虽然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并不存在“米兰达警告”的惯用语境和程序,但米兰达规则的核心精神——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权——也均被明确于我国的法律文本当中。当然,由于中国具有较长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侦查习惯,沉默权在中国的确定颇经历了几番波折和反复,但最终也在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得以明确。
通过米兰达规则,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在强势傲慢的国家机器面前,沉默,是一种尊严。
主要参考文献:
1.孟军:《艰难的正义:影响美国的15个刑事司法大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2.赵娟:《美国米兰达规则的适用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以2010年美国两榜最高法院鲍威尔案为例的评析》,《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金华:《米兰达规则的蜕变及其启示》,《武陵学刊》2010 年第5期。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