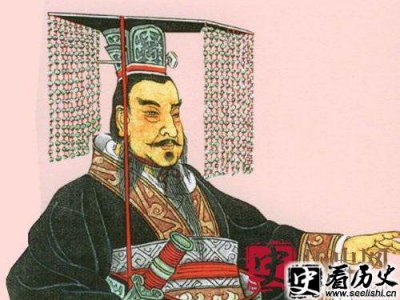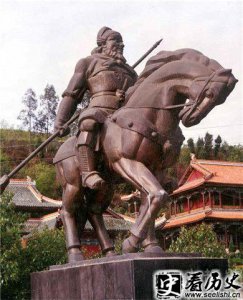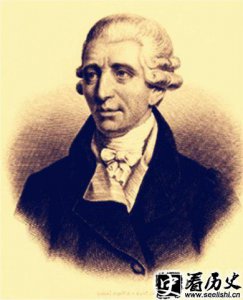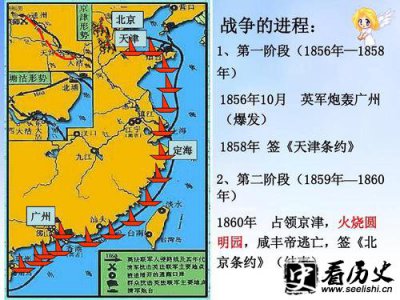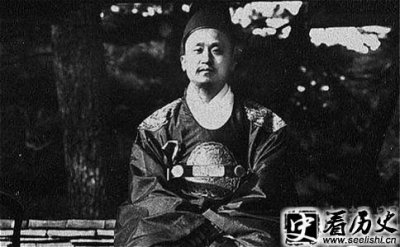唐朝诗人宋之问生平 宋之问结局 宋之问子女 宋之问作品
唐朝诗人宋之问生平 宋之问结局 宋之问子女 宋之问作品
水分清浊,山分雄秀;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一个人的开始与他的后来,也有一比。《论语》里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君子有成人之美”,道德的修行,品质的磨砺,人格的历练,是几千年来关乎人生的一个终生话题。而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评判,有时几经反复,历时久远,才能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一千次的口诛笔伐,并非意指一人,而是在评判的同时,将具有普遍批评价值的皮鞭落在了向善之人的心坎上,从而推动社会道德的整体提升,确有“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无穷威力。
说要唐代诗人,不能不提宋之问。一直想跳开这个毁誉不断的人,但他确是唐朝诗人中独特的“这一个”。宋之问的一生,从向名到追名,从成名到毁名,从名败到身殁,他自己也许浑然不觉,一生诗意陶然。
平心而论,宋之问是个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十年寒霜苦读,不仅为他赢得了功名,也为他赢得了诗名。在年轻的时候,就与“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他比杨炯还要小五六岁)一起分配到习艺馆,这是一份没有实权但很体面的工作,文章才气渐渐知名。后来,武则天因为欲掩丑声,令人编撰《三教珠英》,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共有一千三百卷之多,主要编译以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为首的儒佛道三家精言。宋之问在参与这项工程之时,结识了当时诸如张说、刘知己、沈佺期等文化名流,过着“日夕谈论,赋诗聚会”的惬意日子。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唐诗纪事》
初唐后期,武则天掌控着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宫廷诗人群会,游幸龙门时举办的这场诗歌大赛,大臣们一字排开,奉旨作文,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奋笔疾书,皇帝考大臣,场面当时相当的引人瞩目。左史东方虬率先成诗,武后大悦,当即赐锦袍一件,东方先生感激涕零地捧着锦袍,叩谢皇恩。可没过多久,当宋之问写好呈上时,武则天看了赞不绝口,觉得意境更胜一筹(这首应制诗的尾句“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可谓将马屁拍得又正又准),又随手将东方先生手中的锦袍夺下,给了宋之问。转瞬之间,锦袍易主。东方虬的难堪是可以想见的,宋之问的喜悦是浮于言表的。

这一次诗赛,点燃了宋之问内心深处的无限虚荣,原来可以因诗而名,由文而贵。
从此宴游不得息。王公贵族大摆车驾出行郊游的队伍里,少不了宋大才子。宋之问的锦绣文章,应景之作,歌功颂德的务虚文采,成了士大夫贵族消闲取乐的风雅之物。“凤刹侵云半,虹旌倚日边”,“今朝万寿引,宜向曲中弹”,“芳声耀今古,四海警宸威”,“微臣一何幸,再得听瑶琴”……勤奋而有天赋的宋之问,用最华美的词藻,最虚夸的色调,最动听的颂词,描述着他所能有幸参与的每一次吃喝玩乐。凭借诗歌驰骋文场,结识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写诗作文,赐金赏银,博得夸赞,为他带来了无限风光。
美酒喝坏了宋之问的脾胃,也喝坏了他的大脑。其间,他攀附上了武则天的宠男张易之兄弟:
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新唐书·宋之问传》
文人的悲哀,不在于能否写出好文章,而在于操守的丧失。宋之问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史上没有过的女皇执政,史上没有过的乾坤颠倒,他们碰到了。但史上文人的节气与风骨,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也可能经过痛苦的思考与抉择,也可能有过无奈与彷徨,可惜最终他们在热酒的蒸腾之下,投入了权贵的怀抱之中,以致甘愿为之炮制文章,代做枪手,而且趋之若鹜,甚至不惜“奉溺器”。在名节与官位上,宋之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且是,谁的声势大,就往哪家跑。写文章的人,沦落到这种地步,颇有些文丐的味道,诗才变成了诗奴。而且,宋之问貌美,长相很好,虽不比张易之那样的“莲花面首”,但还是比较出众的,当年还曾有过谋求武则天小蜜职位的举动,因为有“齿疾“(口臭)的毛病,没有得到同意。否则,宋之问大约还要风光一些。
标签: